煤矿作协4人上榜中国作协 倾情畅言“我的作家之路”
-
- 发表于:2022-10-17 浏览量: 1523 来源: 中国煤炭报
日,中国作协公布了2022年会员发展名单,中国煤矿作协4人上榜:河南能源集团义煤公司王晓峰、中煤集团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孔庄煤矿吴允锋、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张春喜、徐州37中(原徐州矿务局第一中学)退休教师曾宪涛。本报特邀四位作家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,分享创作心得体会,旨在鼓励煤矿文学爱好者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。

文学之光照亮人生
■张春喜
我从上大学开始,系统学习文学专业课程,文学审美逐渐提高,视野也变得开阔,算是正式开启了文学创作,到现在已有三十余年。我今年加入中国作协,了却了一个夙愿,人到中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我从小就爱读书,那时候,农村的书特别少,凡是能接触到的书都看,读着读着,遣词造句就有了语感,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表扬。初中时开始向报刊投稿,陆续有一些作文发表,也获了几个作文大赛奖。上高中以后,写了很多诗歌、散文,发表了五六十篇(首)作品。在当时中学生写作群体里,算是有一点小名气。1991年,我被江苏教育出版社评选为首届“雨花杯”全国优秀文学少年,同年被路遥、贾平凹、杜鹏程、胡采、李若冰、白描等著名作家联名推荐,作为文学保送生进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深造。所以说,我是文学的受益者。
进入大学以后,我才知道吉林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,杨振声、冯文炳(废名)、张松如(公木)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教学。在我刚刚学习写诗的时候,学长丁国成、徐敬亚、王小妮、吕贵品等人已成为著名诗人,还有很多学长也一直活跃在文坛上,我作为后来者压力倍增。大学期间,我陆续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。1993年,我23岁,加入了吉林省作家协会,是当时最年轻的会员。
大学毕业后,我从诗歌创作转向了小说创作。每到周末,我就提一壶开水,带一包方便面,到办公室去写,中午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儿。写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很多稿件都石沉大海,有的稿子两三年都发不出去。那时候,我经常在想,现在生活有保障,为什么还要受这份罪呢?稿子投出去后石沉大海是对写作者最大的折磨,到底是自己写得不好呢,还是编辑部看不上咱这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?偶尔,我也能收到退稿信,是油印或打印的一小张纸,写着我的名字和稿件名称。收到的手写退稿信特别少,只有几封。在石沉大海和退稿之外,收到用稿通知的惊喜也有一些,那是对一个勤奋写作者的奖励,鞭策我努力提高稿件质量。
创作长篇小说《方城记》历时十年,充满了艰辛。因为是业余写作,时间是碎片化的,所以有时间就写一点。间隔的时间长了,情节都陌生了,经常要重新把前面的篇章温习一遍,才能接着写下去。最头疼的是修改,每次打印像砖头那么厚的一沓纸,改了一遍不满意就再改,纸上改了再在电子版上改,改过十遍之后,才交给出版社。
如果说写作有捷径可循的话,那就是要学习名家大师的作品,不仅要学,还要悟。我曾一度十分迷恋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,不仅细致阅读了他们的大部分作品,还写了一些评论。他们的作品既有“匠气”,也有“才气”,还有一种文学的“大气”。后来也读了莫言、余华、苏童和金宇澄等人的作品,觉得北方作家和南方作家写作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比如,北方作家的长篇小说普遍显得奔放、恢宏、厚重,有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思考。南方作家的长篇小说则显得细腻、内敛、温婉,于时间的碎片中将生活细嚼慢咽,折射出生活的无奈和沧桑。我的这个认识不一定对,算是一家之言。
我生在北方,长在北方,我的骨子里有北方人特有的那种“硬气”,体现在性格里,用陕西人的话讲就是“刚梆硬正”,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“文学正义”。因此,我的作品就是我人格的化身,我不追求“著作等身”,也不追求名利双收,但是我希望我可以用文字书写正能量。
文学写作要耐得住寂寞。写作是我的人生理想,坚持了半辈子,已经无法割舍。坚持写作很难,我身边的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放弃了。我坚持写作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我对文学的挚爱和执著,这是少年时的一个爱好,成为作家或许想过,但并不强烈。那时候,我最迫切的愿望是考上大学,实现跳出农门的目标。在大学接受了正规的文学教育之后,觉得要写出名堂没有那么容易。后来写着写着,就不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,有了用文字表达观点的想法。二是我对写作没有名利追求,没有要成为一个“著名”作家的迫切愿望,显得有些“淡泊”。
这些年,我扎根煤炭行业,以一己之力为煤炭人书写历史,我觉得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,因为煤矿人身上的吃苦精神和奉献精神时时感动着我,让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笔。我也要感谢煤炭行业,让我有机会获得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。我获得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,也是因为写了一篇关于煤矿小说的评论。加入中国作协也是由煤矿作协推荐的,我和煤矿有着很深的缘分,煤矿是我文学创作的富矿,文学之光和煤炭的火焰将我的人生照亮。

始于听大鼓书
■王晓峰
听 书
从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作家。
我的童年是在豫西农村度过的。那时候,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,没有电,更没有电视,放一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。因此,一到晚上,在田里忙了一天的农民都是早早上床睡觉,来节约灯油。当然,也偶尔有充实的时候,那就是村里来了说大鼓书的。
说书人来的那一天,村里大部分人家晚饭吃得都会比较早。放下碗,村民就呼朋唤友、三三两两搬着凳子向村头的打麦场涌去。那里地势开阔,是说书人固定的表演场所。点上一盏臭石灯,搬来两张桌子、几把凳子,一个说书的场子就搭好了,有好心的人家还会为说书人摆上几个粗瓷大碗,放上一壶开水。
那时流行的大鼓书主要有《杨家将》《呼延庆打擂》《三侠五义》等,现代的也有,如《平原枪声》《烈火金刚》等。故事情节大都是记不住的,留在记忆深处的只是打麦场上的那种氛围。
借 书
我们村属于比较小的村子,小村子是养不起说书人的。因为一部书很长,几天时间根本说不完,只好和其他村子联系续着说,于是我们这些孩子便翻沟越岭撵着说书人去听。即便如此,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,有听不完整的时候。
书听到一半,没有了下文,心里就像装了一窝兔子,百爪挠心。我喜欢看书,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那时候,书不像现在这么多,所以,只要一拿到书,就猛“啃”起来。
我有一个姓冯的同学,其父藏书颇丰。我常常向他借,他一开始不肯借。后来,我俩终于达成了协议:每天早上,我喊他一起上学,他供我书看。我妈支持我学习,但不支持我看那些课外书,怕那些闲书影响我学习。也确实如此,我只要一看上书,就会沉浸其中。有时好不容易得到一本好书,第二天说不定又给人要去,就借口学习,躲在我的小屋里看起来。最糟糕的要属晚上,书看不完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于是就点起煤油灯,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。为了怕妈妈看见灯光,就用四五层报纸把窗户堵上。有时还会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书,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第二天晚上妈妈去浇地的时候才发现手电已经没电了。妈妈摇摇手电筒:“你说怪不,刚买的电池,没用几天,咋没电了。”一节电池五毛钱,在那时候是很贵的,我却不管这些。因为恋上了读课外书,忽略了学习,1985年,考学无望的我步了父亲的后尘,到义马矿务局常村煤矿当了一名矿工。
写 书
每天10多个小时繁重的井下工作,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危险因素,使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:难道我就这样一辈子待在煤矿井下吗?我不甘心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开始了写作。最初写作的念头,就如刘庆邦老师小说《红煤》中的主人公宋长玉一样,想通过写作让别人认可自己。
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是一篇小小说,题目叫《愧》,写的是年终评先的故事。故事情节很简单,现在看起来自然很幼稚,但在那时,对我来说,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写好后,我贴上邮票,郑重地寄给了《义马矿工报》。也许是编辑不愿打击我的积极性吧,就给我发了,尽管删到只剩下四百多字,仍然让我高兴了好多天。
因为会写文章这么一点“专长”,我被调到矿安检科,后来又被借调到矿党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,业余时间写新闻。为了能留在机关,我坚持每天不少于两小时阅读报纸,还剪贴了几大本简报。
付出总有回报。写得多了,在矿区小有名气了。后来,义煤集团总医院招聘文秘和写作人才,我凭借厚厚的几本发有我文章的剪贴本,被成功录用。
写新闻久了,总觉得有点意犹未尽。矿区生活的点点滴滴,矿工兄弟的逸闻趣事,有些不适合用新闻来表达,我就想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。于是,就又捡起了放下许久的小说写作,也就有了《余矿长》《林梦兆》《喜成娘》《马欣超》《山杏》《晚来》《漆雕》《封建》《刘美丽》等一系列矿区人物小说。这些作品,后来陆续发表了。随着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,我所写的体裁也越来越广泛,不仅写小说,还写散文和文学评论等。凭借这些成绩,我不仅加入了中国煤矿作协、河南省作协和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,而且还结集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和一本新闻作品集。今年,我又荣幸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加入中国作协,对我来说,是鞭策,更是鼓励。作为一名矿工,一名矿工的后代,我会始终如一地关注矿区,关注矿工,努力用手中的笔去写好属于矿工自己的故事。

从翻砂工到作者
■曾宪涛
我从小好奇心重,喜欢探秘,爱好理科,梦想将来成为一名天文学家,从没想过当作家搞文学创作。我感觉自己的逻辑思维要比形象思维好,缺少文学写作方面的天赋。
小学五年级赶上特殊年代,停课在家三年,后来初中复课一年,便进了工厂,干翻砂工。那时我16岁,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。后来我成为一名老师,上课时常给高中学生讲,高中是人生的黄金时代,是求知欲最强、最需要学习的时期,要珍惜啊。可我的黄金时代却没机会学习。
翻砂工干的是工厂最苦最累的活,车间里嘈杂轰鸣,沙尘弥漫,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简单而繁重的劳动。工余时,我蹲在砂箱上,望着从天窗上射下的一束光柱,看着飞尘滚滚,开始思考: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了?那是我人生最苦闷的日子,身体的苦不算啥,苦的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。我不想就这么过一生,却又找不到方向。我消极沉闷,父亲说我颓废,还教育我行行出状元。我冒出一个念头,可以钻研一下技术,翻砂工有八级,技术无止境。我去书店买了本《铸造工艺学》,钻研了很久,才知道一点用不上。我们干的是行板活,模型都在行板上固定好了,只要有力气就行,技术上的事不用操心。
那时年少,自认为聪明才智无用武之地,每当读李白那句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时就想哭。人的苦闷不能老憋着,总要有个地方发泄出来。我开始学着写诗,想通过写诗排遣自己的郁闷,抒发情绪。我把写好的诗给一个好友看,他说要是以前肯定能发表。这便激发了我的兴趣,开始了不知算不算得上文学创作的写作。后来我写过两首长篇朗诵诗,还在市局的朗诵比赛中获了奖,厂里聘我为工人通讯员,送我去广播电台培训。这对身为翻砂工的我来说,简直受宠若惊。写作给我带来了快乐和自信,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我后来写小说,是受了两部作品的影响,一部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另外一部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。在最需要读书的阶段,我看过的书少得可怜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母亲的一本书,我反复看来看去,这本书对我影响最大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,是在书店买的三本小画册,原著当时很难买到。我感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与两位主人公都有相通的地方,我也想写本自传体小说。
我经常说,我搞文学是先天不足,后天缺养。在我二十多岁前,几乎没看过什么世界名著,写作也是从“三突出”学起的,所以写作时断时续。
后来恢复高考了,我就停下了写作,因为要学习备考。之所以说是学习,而不是复习,是因为我正式上学也就到小学五年级。有人笑话我,说我这小学没毕业的水平还考大学。但我想抓住命运给予我的机会。1977年有个初始试,只考语文数学两门,我数学交了白卷。考后便发誓要学好数学,用了半年时间,我把一本大专数学教材啃了一遍。因为当时只买到了这本教材,啥也不懂,以为是数学就行。1977年高考是冬季,1978年高考是夏天,我至今还记得考前的难眠和考试时脊背上流下的汗珠。我拼了全力,考入了大学。上完最后一个中班,出了厂门,回望着黑乎乎的大车间,我流泪了。
上大学期间,那是中国文学最火热的年代,很多作家的成名作都是那个年代推出的。我常想,假如没上大学,会不会也能写出什么名作。
毕业后我被分到煤矿中学工作,才真正开始了创作。我家人都在煤矿工作,到矿区后我更加了解了矿工。我感觉翻砂工和矿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我熟悉他们,跟他们有感情,我的作品是写给他们看的。每回跟矿工报的记者去矿上下井,望着那高高的矸石山,我仿佛看到了矿工用双手在地下挖煤的场景。回到家,我写了篇散文《心中的大山》,后来这篇散文还获了奖。发表时,编辑部的编辑要我写句话,我还记得,我写下的是“站在老百姓的角度,写老百姓的故事”。
上世纪90年代以后,我又停笔了,主要是那时的小说叫人看不懂了,无主题、无情节、无人物的三无小说也出来了。我不懂写这些东西干啥,文学难道也追求时髦?你抛弃了读者,也就被读者抛弃。
进入新世纪,我感觉传统的东西似乎又回来了,2006年重新拿起了笔。
我写作不追求高雅高深,而是希望读者能喜欢。我经常说,做人要雅,写作要俗。“俗”就是要大众,不要小众。我的一些作品,后来被用作中学语文试题。我写的东西对孩子们有用,让我倍感欣慰,毕竟我是当老师的。
中国作协接纳了我,这是对我创作的肯定。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,写具有中国气派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。

河的对岸
■吴允锋
“一条铁路的旁边一定要有一条河吗?”
我们村子的东边挨着一条河。河的对面有条铁路,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。它是大屯煤电公司自营铁路的一部分,向南延伸约60公里,并入国铁陇海线。因为有铁路在河的东岸,所以我们常把这条河叫铁路河。1967年出生的我,放学后常坐在河的西岸,看对面的火车南跑北奔,奔跑的火车给了我无边的想象。一条河,阻隔了小小少年对火车的亲近,才生发了上面的疑问。对被河流隔阻的辽远与神秘的探寻,也恰是一个乡村少年的梦想。直到有一天,河上出现了桥梁……
令我没想到的是1987年中专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大屯煤电公司工作。当时,煤电运综合经营的“大屯模式”在煤炭行业内很有名。恍惚间,我在大屯煤电公司已工作生活了36年。一边紧邻农村老家,一边又置身煤炭国企,从青年时代起,在思想或精神层面上,我就在不断地接受着两种力量的争夺。一种源于古老的农耕文化,一种来自现代的工业文明。至今,都无法摆脱两者对我的争夺,我亦无法让两者在认知里达成统一。或许正是因为深陷这种困境,才促使我走上了写作之路。
我出过两本集子,一本叫《沉浸》,一本名为《次悲伤》。前者多是对家国往昔的追溯和依恋,后者则侧重对当下生活的描摹与思考。大屯煤电公司所在地以前叫大屯镇,我们村就在镇内。我曾以《大屯镇》为题写过一首诗,结尾写道:“在大屯镇/那些人们赞美过的,我仍将赞美/那些人们原谅了的,我在学着原谅。”这是我的乡村态度,也是我的生活理念。
当你拿起笔进行写作的时候,经常会有人问你写作的意义。1989年,我在《诗刊》上发表了《鲁迅在中国挖了一口井》:“鲁迅把井里的清水提上来/鲁迅把井里的苦水提上来/鲁迅把水盛在景德镇的大瓷碗里/给人喝。”这是我写作最初的动力,在阅读中被鲁迅吸引、激发。我崇拜并追逐着鲁迅的脚步。鲁迅是中国写作者的一个标杆,他的深刻和凝重,既是时代塞给他的,也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,深刻和凝重本身就是意义。
当年读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,最打动我的一句是“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/我将告诉每一个人”。这句诗本身就像一道闪电把我击中,我突然意识到了写作对我的意义:传达美好或弥散悲伤。
大约在十年前,有一次我到山西出差。在大运高速平遥段,行驶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越野车突然侧翻。我看着男车主慌乱中在拨打电话,手指因颤抖无法按准号码。与他同行的女性头上流着血,痛苦地靠在隔离带上。一个小女孩则赤着双脚,惊恐万分地站在满地的碎玻璃上。我们帮忙把人带到安全区域,摆放好警戒标志。当时我手边有一枚熟透的芒果,我走到小女孩身边,蹲下身把芒果放到小女孩的手里,悄悄在她耳边说:“请拿好这枚芒果,它有好闻的香味,它是上天派来保护你们的。”说完,我注意到了小女孩的神情有了细微的变化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悲伤中的一个美好的细节,我觉得它是。回来后,我用一首《一枚芒果闯入惊恐中》记述了那段经历。
1995年到2005年,在那横跨世纪的十年,我的写作按下了暂停键。原因是世相纷乱,我心亦乱。相比那些优秀的诗歌写作者,我自感天赋有限,学识不足,可能终其一生,也写不出什么特别像样的作品。于是,我放下了笔,抛开作者的身份,以一个单纯的生活者投身生活,单纯地去体味生活的悲喜。体味的时间久了,我心内又暗暗地生出了书写的冲动。有人说我这段时间在沉潜,其实我知道不是的,我只是顺着自然停下的。当我重新回到写作现场,人已变得轻松和温和,写作成了我的一种表达方式。这样的心态,使我发现写作依然如此美好。
栖身煤企三十余载,经历过煤企的几度兴衰,也一次次体会了煤炭人的朴实和艰辛。有一次在井下的猴车上,突然听到一阵歌声,是对面一个满脸煤灰的矿工弟兄在吟唱。我写下了“我的矿工兄弟们,在深渊里/拯救一种叫煤炭的事物”。
靠近美好本身就很美好,写作无疑是靠近美好的一种方式。希望相随,有梦最美。当年,在铁路河的西岸,少年对对岸火车的好奇和对远方的遐想,沿着美好之路,追寻美好的源头。写作不仅给了我梦想,也让美好变得可近、可及。
一条铁路的旁边当然不一定要有一条河,少年的疑问早有了答案。但在你和你仰望或观照的每一件事物之间,都有着一条河,不论它是时间之河、空间之河,还是人世之河。随着我日复一日不懈的泅渡,我的写作梦也在河的对岸不断地展开……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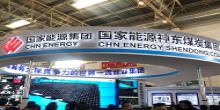



JMJTWWH :讲的不错
13856114361 :可喜可贺,可喜可贺
hbky32945 :人生既是如此,有梦想就有更好的未来。
13855477065 :